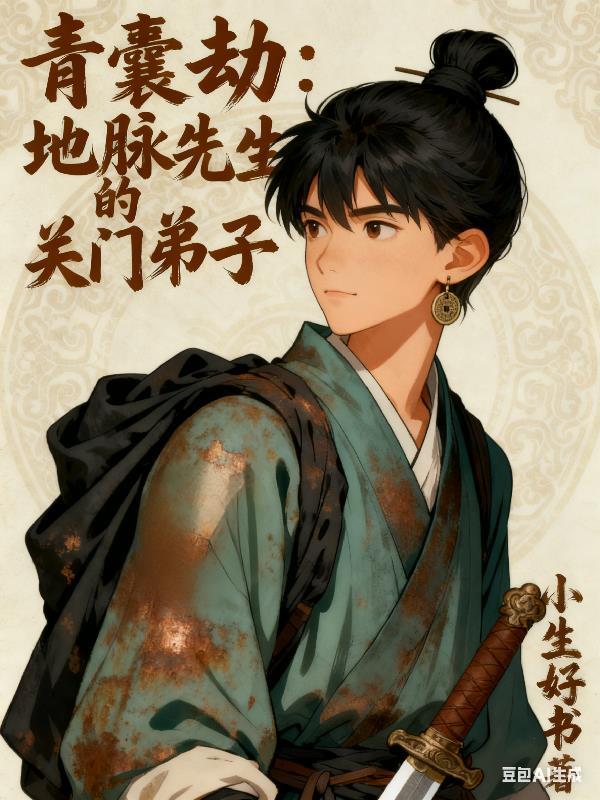书籍简介
首章试读
西南边陲的雨,总带着股化不开的潮气。 陈观棋叼着根狗尾巴草,坐在吊脚楼的竹编栏杆上,看着雨丝斜斜打在对面的山壁上。那山像头卧着的老兽,青灰色的岩石被雨水浸得亮,岩缝里钻出的野藤垂下来,被风一吹,晃晃悠悠扫着楼底的泥地。 吊脚楼是木头搭的,少说也有几十年了,每根柱子都透着股陈旧的木香,混着雨水的腥气,成了陈观棋闻了十七年的味道。他今年二十岁,可这楼里的每道木纹、每处磨损,都比他的记忆更长久。 “咔哒。” 里屋传来龟甲裂开的轻响,陈观棋吐掉嘴里的狗尾巴草,翻身跳进屋里。 地脉先生正蹲在矮桌前,指间捏着半片龟甲。老人头灰白,用根木簪随意绾在脑后,露出的额头上刻着几道深纹,像是被山雨冲刷过的沟壑。他穿件洗得白的粗布道袍,袖口磨出了毛边,可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,此刻正盯着龟甲上的裂纹,眉头拧成个疙瘩。 “师父,又在卜啥?”陈观棋凑过去,鼻尖差点碰到矮桌上的罗盘。那罗盘是铜制的,边缘磕掉了一小块,盘面的刻度被常年的摩挲磨得亮,指针却总在微微颤动,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底下拉扯。 地脉先生没抬头,捏着龟甲的手指关节泛白:“张屠户家的新宅,明日你去看。” 陈观棋“哦”了一声,目光落在桌上那半本泛黄的书册上。书皮早就没了,纸页脆得像枯叶,边角卷着,上面用毛笔写的字却依旧清晰,正是《青囊经》的残卷。这是他三岁被师父从战火里捡回来时,唯一被塞到怀里的东西——除了左耳那枚铜钱耳坠。 他下意识摸了摸耳坠,铜钱边缘被磨得光滑,中间的方孔刚好能穿进一根红绳。师父说这是他的“本命钱”,能挡灾,可陈观棋总觉得,这玩意儿更像是个标记,提醒他来路不明,像这吊脚楼外的野藤,不知道自己的根扎在哪。 “师父,张屠户家那宅子,我前几日路过瞧过一眼。”陈观棋拖了个竹凳坐下,学着师父的样子,手指在桌面上画着无形的线条,“背靠鹰嘴崖,前有小溪绕屋,按《青囊经》上说,这叫‘玄武垂,朱雀衔珠’,是吉地啊。” 地脉先生终于抬了眼,那双眼睛里像是盛着山涧的水,清得能照见人心里的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