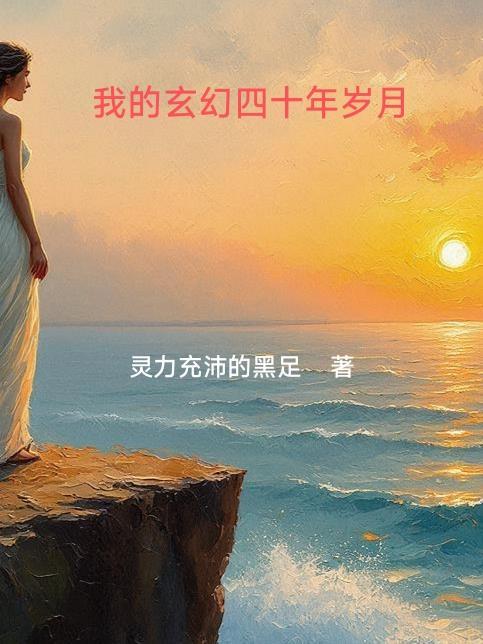书籍简介
首章试读
慕景沫第一次现自己的“异常”,是在处理一份过期合同时。 窗外是城市永不疲倦的霓虹,办公室格子间早已人去楼空,只剩下她工位头顶一簇惨白的灯光,固执地切割着黑暗。她揉着酸胀的太阳穴,指尖不小心划过合同末尾那个早已失去法律效力的公司印章——触感冰凉。 就在这时,意想不到的事情生了。 那枚鲜红的印泥痕迹,竟像被赋予生命般,从泛黄的纸张表面“浮”了起来!它不再是一个二维的图章,而是化作一滴粘稠、暗红、似乎还在微微搏动的液滴,静静悬浮在纸面之上几毫米处,散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腐朽气息。 慕景沫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缩回手,背脊瞬间爬满寒意。 幻视?加班过度的后遗症? 她定了定神,再凝目看去。那滴暗红的“血印”依然悬浮着,甚至边缘还蒸腾起一丝几不可察的、带着陈年尘埃味道的红雾。它像一滴沉甸甸的、凝固的时间污渍,一个来自过去的、令人不安的具象回响。 这绝不是第一次。最近……越来越频繁了。 收拾完东西走出冰冷的大厦,初秋的夜风已带着凉意,吹散了那点残留的晕眩。她习惯性地裹紧外套,手指无意识地拂过外套内侧某个不起眼的衣领边缘。那里,有一小块极淡的、仿佛不小心沾染的墨迹,只有她自己知道,它并非源自墨水。 一周前,翻阅一本陈旧童年日记时,其中一行歪歪扭扭、写着“爸爸骗人,他明明说好今晚回家”的字迹,就这么化成了几滴黑色的、冰冷咸涩的水滴,“啪嗒”一声落在她的睡衣上。那冰冷的触感和浓郁的悲伤,让她一夜无眠。 她的名字,慕景沫——“仰慕景致,浪沫浮生”——似乎正被赋予某种诡异而精准的字面意义。时光的“景”,在她眼中不再仅仅是流动的光影,而是化作了字与句;而生命的“沫”,也正从那些承载过情感或誓言的文字中逸散出来,具象成为现实的投影,短暂而脆弱地停留在她的世界里。 回到她那间小小却整洁(或者说是刻意保持整洁来对抗某种内心混沌)的出租屋,慕景沫卸下一天的疲惫,目光却不由自主被床头柜上那本特殊的笔记本吸引。 那不是普通的笔记本。硬壳封面没有...